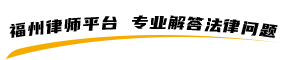一、基本案情
2013年7月8日至2017年8月2日期間,姚某、方某駕駛車輛在某地區收費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跟車的方式,多次偷逃高速通行費,共計人民幣近萬元,后被抓獲。
二、罪名爭議
(一)構成尋釁滋事罪。逃繳高速公路通行費顯然破壞了高速公路正常的運行、發展秩序,損害了社會公共秩序,行為人應當支付通行費而強行不支付的行為可以認為是強拿硬要。
(二)搶奪罪。行為人趁收費員不備以跟車通過欄桿的方式逃費,具有公然性。
(三)盜竊罪。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采取秘密手段通關的認知,客觀上沒有采取暴力等行為,也具有“秘密”屬性。
(四)詐騙罪。行為人隱瞞了其不想支付高速通行費的主觀目的這一心理事實,而通過拿卡進入高速公路這種形式假裝有支付通行費的意思表示,從而讓對方提供高速公路服務,這無異于“無錢飲食、住宿”,符合事實欺騙的特征。
三、符合搶奪罪、尋釁滋事罪的構成,擇一重罪處罰(當數額不大都為基礎刑的時候,尋釁滋事罪重于搶奪罪;當數額大到搶奪罪跳檔,而尋釁滋事罪仍為基礎刑的時候,搶奪罪重于尋釁滋事罪。)
厘清行為手段性質準確界定相應犯罪構成
作者:田宏杰(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以跟車方式逃避交納車輛通行費,應當如何定性處理?對此,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實務部門,均歧見紛呈。筆者以為,逃避交納車輛通行費案件的性質認定,必須厘清以下兩個問題:其一,拒交、不交或少交車輛通行費行為的違法本質究系如何,是單純的侵財還是對社會管理秩序的破壞?其二,以跟車方式逃避交納車輛通行費的行為,在刑法上應如何認定制裁?
偷逃通行費行為侵害法益定位分析
對于上述問題,筆者歷經多年研究并在司法實踐中不斷檢驗完善提出,無論刑事犯罪的立法規制還是司法適用,在中國法制語境下均應秉持“前置法定性與刑事法定量相統一”的刑事犯罪認定機制。因而逃避交納車輛通行費行為之違法實質的準確把握,關鍵在于對車輛通行費的收取予以規制的前置部門法及其所承認確立并予以法體系首次法律保護的前置法法益的確定查明。按照2004年施行的《收費公路管理條例》(下稱“《條例》”)第 1條的規定,《條例》制定的目的在于“加強對收費公路的管理,規范公路收費行為,維護收費公路的經營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公路事業的發展”。基于此,《條例》明確要求,收費公路的收費期限,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按照第14條規定的標準審查批準;車輛通行費的收費標準,應當依照價格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進行聽證,并按照第15條規定的程序審查批準;收費公路經營管理者收取車輛通行費,必須按照第32條的規定,向收費公路使用者開具收費票據。同時,收費公路經營管理者負有依照國家規定的標準,設置交通標志、標線,承擔收費公路養護、綠化等義務。由此可見,車輛通行費表面上關涉的是所收款項的財產權益,實際上是收費公路經營管理秩序的有機組成,兩個法益之間是部分與整體的包含關系。故而拒交、逃交、少交車輛通行費等故意堵塞收費道口、強行沖卡、毆打收費公路管理人員等行為,表面上侵犯的是所收、應收車輛通行費的財產權,實際上妨害的是收費公路的正常經營管理秩序。由于收費公路的經營管理活動并非依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的經濟行為,而是按照《條例》規定實施的社會公行政即路政管理行為,所以,收費公路的經營管理秩序并非我國現行刑法典分則第3章致力于保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下位概念,而實屬現行刑法典分則第6章所維護的社會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
妨害通行費收取行為方式及定性界分
囿于社會現象尤其是社會失范行為的紛繁復雜,妨害車輛通行費收取的行為方式亦多種多樣,歸納起來不外以下方式:一是秘密進入收費系統或收費箱,從中竊取車輛通行費據為己有的;二是針對車輛通行費不同收費標準的適用條件弄虛作假,以不交或少交車輛通行費的;三是以強行沖卡、快速跟車等方式,趁放行前車的橫桿尚未落下,在收費工作人員眼皮底下疾駛揚長而去的;四是以暴力、脅迫或其他相當方式,逼迫收費工作人員放行以拒交、不交或少交車輛通行費的;等等。顯然,上述行為在違法本質或法益侵害實質上,均具有財產法益和收費公路經營管理秩序的雙重法益侵害性,因而對其不法性質的完整認定和刑法處理,還應進一步厘清其妨害手段的性質,方能最終判斷并確定其所符合的犯罪構成,從而定性處理。
應當說,上述各妨害收費公路經營管理秩序的行為方式的性質及其相互之間的界分,從侵財角度而言,本十分清晰,即第一類系以盜竊為作案方式,第二類乃典型的詐騙方式,第三類則以搶奪為手段,第四類的手法顯系搶劫。但近年來,隨著對域外刑法研習的深入,盜竊、搶奪、搶劫之間的界限反倒模糊起來,尤其是對于秘密竊取之“秘密”的內涵和解讀,學界就有“平和說”“公然說”“不為被害人認知說”等,莫衷一是。
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日本刑法雖然今生多借鑒德國刑法,但其前世卻多承襲中國唐律。而中國封建刑法中的個罪歷史,除劉邦入函谷關所昭告天下的“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人身犯罪外,財產犯罪實如老子所言: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其中,盜指竊盜,即以秘密方式侵財;賊謂強盜,即以人身強制包括身體強制和精神強制在內的強力手段侵財。因而盜所侵犯的法益僅限于財產權,而賊所侵犯的法益則既有人身權,又有財產權,且人身權的侵害實乃手段,財產權的侵害才是目的,所以,盜乃今日所謂之盜竊罪,賊即現代所言之搶劫罪。至于我國現行刑法第267條規定的搶奪罪,在中國封建刑法中并無專門的罪名。
新中國成立后的兩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和1997年現行刑法典,則在傳統盜、賊的基礎上,從中分離演變出盜竊罪、搶奪罪和搶劫罪。質言之,搶奪罪系從以往盜竊罪和搶劫罪中抽取部分而形成,指非但不為被害人不知,而是以與被害人直面相對,甚至有人身接觸乃至輕微人身強制的手段非法侵財,但人身接觸乃至輕微人身強制尚不足以構成侵權法上的人身侵權,從而仍只具有單純的財產侵犯性質的行為。例如,行為人尾隨從銀行取錢出來的被害人,趁其不備,對其拿有錢包的手腕用掌一擊,被害人松手致錢包落地,行為人遽而抓起錢包逃跑等,即是搶奪罪的適例。而這才是搶奪罪有別于搶劫罪的本質區別所在。正因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關于辦理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6條規定:“駕駛機動車、非機動車奪取他人財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㈠奪取他人財物時因被害人不放手而強行奪取的;㈡駕駛車輛逼擠、撞擊或者強行逼倒他人奪取財物的;㈢明知會致人傷亡仍然強行奪取并放任造成財物持有人輕傷以上后果的。”與之相反,在上述情形中,如果未造成足以達到侵權法上的人身侵權程度以致足以認定構成人身侵權的,則應論之以搶奪罪而非搶劫罪。
至于盜竊罪的秘密竊取行為,由主客觀相統一的刑法原則和責任主義所決定,則專指行為人以自以為不為被害人所知的方式侵財。因而在車站、機場等人流涌動的公共場所,趁被害人熟睡之機,在眾目睽睽之下,拿走被害人財物的,固然是秘密竊取;深夜入室盜竊,行為人經觀察以為尚未驚動睡夢中人,但其實被害人早已被驚醒,只是基于人身安全考慮而假裝熟睡,行為人繼續取財的,仍得以盜竊論之。
由此可知,跟車逃避交納通行費的行為方式,既不是制造假象讓收費工作人員發生錯誤認識進而放行的詐騙,也不是自認為收費工作人員不知情的秘密竊取,更不是以人身強制進而非法取財的搶劫,而是在前車通過,橫桿尚未完全落下之時,趁收費工作人員不備,快速跟進絕塵而去,從而變一桿一車為一桿兩車,令收費工作人員只能望車興嘆的搶奪。
所以,以跟車方式逃避交納車輛通行費的行為,既符合搶奪罪的犯罪構成,又完全具備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具體系法定第三種行為樣態,即強拿硬要公私財物,擾亂收費公路經營管理秩序的尋釁滋事行為。由于搶奪罪和尋釁滋事罪兩罪在犯罪構成上存在著包容關系,屬于刑法理論上的法條競合形態。因特殊法條往往也是重法條,故而按照特別法條優于普通法條亦即重法條優于輕法條的法條競合處斷原則,從一重罪處罰。而這也正是《解釋》第7條規定的旨趣所在:“實施尋釁滋事行為,同時符合尋釁滋事罪和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敲詐勒索罪、搶奪罪、搶劫罪等罪的構成要件的,依照處罰較重的犯罪定罪處罰。”
就本案而言,由于行為人多次以跟車方式逃避交納車輛通行費累計近萬元,無論其構成的是搶奪罪還是尋釁滋事罪,均應適用基本量刑幅度處罰。由于尋釁滋事罪基本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是五年有期徒刑,搶奪罪基本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僅只三年有期徒刑,相較之下,構成的尋釁滋事罪是重罪,故本案應以尋釁滋事罪定性,依其具體量刑情節,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幅度內科處刑罰。
載《檢察日報》2019.6.14實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