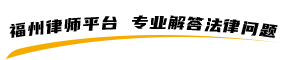從我國現(xiàn)實國情來看,絕大多數(shù)父母在子女購房時的出資目的是為解決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條件,為子女創(chuàng)造良好的物質(zhì)條件,而非日后要回出資,父母對其主張在子女購置房屋時的出資系借貸需承擔更為嚴格的舉證責任。
本案中,父親主張其出借系爭款項用于兒子購房,兒子及母親均否認系借款,從本案實際情況看,在各方仍保持相對正常的夫妻父母子女關系的情況下,鑒于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與親情關系,父親在兒子購買房屋時的出資,以為兒子創(chuàng)造更為良好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的可能性更高。因此父親主張與兒子之間存在借貸合意,要求兒子歸還系爭款項的訴請,難以支持。
2.判令張曉支付以400萬元為基數(shù),按同期全國銀行間同業(yè)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自本案起訴之日2022年8月18日起計算至實際清償日止的利息;
張強與張麗原系夫妻關系,張曉系兩人之子。
2014年4月23日張強與張麗登記離婚。
2018年11月15日張強轉(zhuǎn)賬給張曉300萬元,2018年11月20日張強轉(zhuǎn)賬給張曉100萬元,共計400萬元。
2017年12月1日張曉與案外人吳某簽訂房地產(chǎn)買賣合同及補充協(xié)議,約定張曉購買本市浦東新區(qū)XX路XX弄XX號XX室房屋,總價600萬元。
張麗于2017年11月30日支付5萬元,2017年12月4日支付295萬元,2017年12月21日支付180萬元,2017年12月25日支付20萬元,2018年7月24日支付500萬元。
張曉于2018年11月15日支付595萬元,于2018年11月16日支付中介公司13.4萬元,于2018年11月22日交納稅款98萬余元。
2018年6月12日張曉與案外人許某簽訂房地產(chǎn)買賣合同及補充協(xié)議,約定張曉出售本市浦東新區(qū)XX路XX弄XX號XX室房屋,總價610萬元。
許某于2018年4月9日轉(zhuǎn)賬支付張曉20萬元,2018年4月20日轉(zhuǎn)賬支付張曉100萬元,2018年6月12日轉(zhuǎn)賬支付張曉230萬元,2018年7月5日轉(zhuǎn)賬支付張曉109萬元,2018年7月23日轉(zhuǎn)賬支付張曉150萬元,2018年7月26日轉(zhuǎn)賬支付張曉1.08萬元,共計610.08萬元。
張曉于2018年4月20日轉(zhuǎn)給張麗100萬元,2018年6月13日轉(zhuǎn)給張麗230萬元,2018年7月9日轉(zhuǎn)給張麗109萬元,2018年7月23日轉(zhuǎn)給張麗150萬元,2018年7月26日轉(zhuǎn)給張麗1萬元,共計590萬元,除首筆款項外,其余款項交易用途均標注為“房款”。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jù)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jù)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jù)加以證明。沒有證據(jù)或證據(jù)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根據(jù)在案證據(jù),張強與張麗于2014年4月23日登記離婚后至2018年11月期間客觀上仍存在經(jīng)濟往來,2019年3月26日張強在寫給張麗的信件中表示“事件發(fā)生至今已好幾個月”“請求你的原諒,讓我們再重續(xù)前緣”,并向張麗提出重歸于好、擱置夫妻矛盾繼續(xù)操辦孩子婚事及公司經(jīng)營、不再和好并進行財產(chǎn)分割三種矛盾處理方案,2017年9月16日張麗微信告知張曉一家四口要溝通兄弟倆婚房之事以及2018年12月12日張強微信向張曉推薦在售房屋,綜合考量上述證據(jù),相較于張麗在張強與他人經(jīng)濟糾紛中對外所作分居陳述,張強與張麗及張曉之間的溝通交流更具可信度,相較于張強的否認,張曉及張麗主張張強與張麗離婚后至2018年底2019年初仍共同生活共同經(jīng)營的可能性更高。
從我國現(xiàn)實國情來看,絕大多數(shù)父母在子女購房時的出資目的是為解決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條件,為子女創(chuàng)造良好的物質(zhì)條件,而非日后要回出資,父母對其主張在子女購置房屋時的出資系借貸需承擔更為嚴格的舉證責任。本案中,張強主張其出借系爭款項用于張曉購房,張曉及張麗均否認系借款,而張強并未提交雙方之間存在借貸合意的相關證據(jù),從本案實際情況看,在各方仍保持相對正常的夫妻父母子女關系的情況下,鑒于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與親情關系,張強在張曉購買房屋時的出資,以為張曉創(chuàng)造更為良好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張強主張與張曉之間存在借貸合意,要求張曉歸還系爭款項的訴請,難以支持。
一審法院經(jīng)審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規(guī)定,判決如下:駁回張強的訴訟請求。
張強與張麗早已離婚,且于2017年便已徹底分居,不再往來。張麗于2019年在另外關聯(lián)刑事案件中接受***詢問時,明確講到張麗與張強已分居兩年多了,事實上他們也確實于2017年便分居了,該事實未被本案原審法院采信,且對此還予以否認,原審認定事實錯誤。
張強在微信聊天過程中雖曾表達過對兩個兒子的婚事和婚房進行補償,但因張強與張曉、張麗之間的關系惡化,以及張強與張曉打架事件發(fā)生后,張強對于之前愿意贈與的表態(tài)可以撤回,不再進行贈與了。況且,張強當時還講到老廠拆遷時,可將補償款用于對張曉婚房進行適當補償,而張曉購房在先,老廠拆遷在后,故訟爭400萬元轉(zhuǎn)賬不應視為張強對張曉購房的贈與。
張曉在一審期間辯稱,張強向其轉(zhuǎn)賬400萬元系其于2018年轉(zhuǎn)款590萬元房屋出售款給張麗的返回款,故其無需再向張強償還該款,張曉的該辯解意見無事實及法律依據(jù)。因張曉向張麗轉(zhuǎn)款時張強與張麗早已離婚,且已分居,張強并未收到過該款,不應視為張曉已將該590萬元付給了張強。一審法院對于張強與張曉、張麗之間的轉(zhuǎn)款視而不見,卻以家庭、親情角度判決駁回了張強的訴請。因此,原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判決錯誤。張強現(xiàn)請求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實的基礎上,改判支持其上訴請求。
張曉辯稱,不同意張強的上訴請求。訟爭錢款不是民間借貸款,張強和張麗當時一致確認XX路XX房購置的補貼,一審判決查明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且維護了公平正義,彰顯了我國家庭親情方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況且,張曉不同意張強關于2017年便與張麗分居并不相往來的主張,該主張與事實不符,張強所提交的公安詢問筆錄是違法證據(jù),不應被采信。總之,張曉認可原審法院判決,不同意張強的上訴主張,其上訴無事實及法律依據(jù)。
二審法院認為,雖然張強與張麗于2014年即已離婚,但后來雙方在較長時間里仍保持經(jīng)濟往來、共同生活經(jīng)營等,離婚后共同經(jīng)營的公司財產(chǎn)和婚姻存續(xù)期間的夫妻共同財產(chǎn)均未分割。
況且,張強分別于2017、2018年通過微信向張麗明確表示對張曉婚房購置予以補貼、向張曉推薦在售房屋等。故本院對于張強提出其向張曉轉(zhuǎn)賬的訟爭錢款為借款實難認同。一審法院依據(jù)雙方提交的全部證據(jù)所認定的案件事實,從父母子女之間的血緣和親情角度出發(fā),再結(jié)合民間借貸法律關系中借貸合意這一關鍵要素,最終,認定訟爭錢款不構(gòu)成借貸款,進而判令駁回張強之訴訟請求正確,本院對此應予確認。
張強不服,提出上訴,堅持認為訟爭錢款為其出借給張曉的錢款。張強圍繞其與張曉之間的借貸合意并未進一步提供證據(jù)予以證明,本院對此難以采信。張強應當承擔舉證不能之不利后果,其所提相關上訴請求無事實及法律依據(jù),難以采納。
綜上所述,張強的上訴請求,理由與依據(jù)均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事實無誤,適用法律正確,所作判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
?(2023)滬01民終15542號 民間借貸糾紛?案例人物均為化名 僅用于學習用途
來源:麗姐說法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