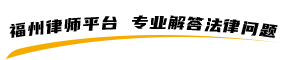【基本案情】福州家事審判觀察匯編。福州家事審判觀察系專業福州離婚、繼承律師–蔡思斌律師在長期關注、搜集福州以及其他地區法院家事審判實例,并結合自身多年辦理婚姻、繼承案件經驗的基礎上歸納、編輯、原創。轉載而成
被繼承人陳丁與李某原是夫妻關系,二人育有三女,即陳甲、陳乙、陳丙。安某是陳丙之子。陳丁于2003年11月2日死亡。
1997年6月20日,陳丁與首鋼總公司簽訂《首鋼出售公有住房合同》,購買101號房屋一套,該房屋于1998年8月8日取得產權登記,房屋產權登記人為陳丁。
陳丁與李某于2000年11月27日經法院判決離婚,該判決認定以下事實:“……雙方在婚姻存續期間分得某小區二居室住房一套,現已交購房款2萬余元,尚未取得房產證,雙方均有使用權。……”關于該房屋,法院最終判決該房屋由李某與陳丁共有,該判決作出后,雙方均未上訴。根據民政局婚姻登記處查詢結果顯示,陳丁未有離婚后再婚記錄。
關于訴爭房屋居住使用情況,自陳丁和李某離婚后,該房屋由二人共同居住使用,后陳丁于2001年5月進入社區養老院居住,該房屋一直由陳丙和李某掌控。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對訴爭房屋是陳丁與李某二人的夫妻共同財產均無異議。
2002年12月10日,經北京市石景山區公證處公證,陳丁立下遺囑一份,內容如下:“遺囑人:陳丁,男,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出生,現住北京市石景山區某托老所,身份證號碼:……。某小區101號房屋是我與前妻李某的共有財產,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院判決我與李某離婚的同時,判決上述房屋小間由我使用,廚房、廁所、門廳共同使用,對上述房屋我擁有二分之一的所有權,我自愿立此遺囑,在我辭世后,將上述房屋屬于我所擁有的份額,遺留給我的外孫安某。”該遺囑右下方為陳丁的簽名及立遺囑時間。
陳甲、陳乙對陳丁在立上述公證遺囑時的民事行為能力持有異議,并提交陳丁于2003年6月12日的住院病案一份為證。該病案載有如下內容:“……入院查體:神志清楚,反應遲鈍,查體欠合作。“此外陳甲、陳乙認為,安某是陳丁的外孫,并非法定繼承人,故該公證遺囑應屬于遺贈,根據繼承法規定,受遺贈人應該在知道受遺贈的一定期限內說明接受遺贈的事實,但安某并沒有按照法律規定作出相應的意思表示,故應當視為安某放棄接受遺贈。安某、李某及陳丙對陳甲、陳乙的上述主張不予認可。
【審理結果】
一審法院作出民事判決:101號房屋的二分之一份額歸安某所有,李某、陳甲、陳丙、陳乙負有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協助安某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手續之義務。
宣判后,陳甲、陳乙不服,提起上訴。一中院作出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二審法院生效判決認為:關于陳丁訂立遺囑時的民事行為能力問題,根據法律規定,十八周歲以上的公民即推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個人,如果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有充分證據證明當事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或者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當經過民事訴訟的特別程序,判決確認其行為能力的具體狀態。本案中雖陳丁的病歷記載為“反應遲鈍,記憶力、定向力、計算力均減退”,但當事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者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認定標準為不能完全辨認自己的行為或者不能辨認自己的行為,故僅依據醫院的診斷,本院尚不能得出陳丁不能辨認或者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結論,陳甲、陳乙在陳丁生前亦未提出確認陳丁民事行為能力狀態的申請。二審期間,陳甲、陳乙提交的證人的視頻錄像并非新證據,亦不能證明陳丁在訂立遺囑時的行為能力狀況。故本院依據現有證據只能認定陳丁在訂立遺囑時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關于安某對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是否如期、明確的問題,陳丁去世時,安某未滿十八周歲,陳丙當時是安某的法定代理人。陳丙獲知遺囑后,將遺囑情況跟李某說明。李某陳述,其知道遺囑情況后,跟陳甲、陳乙作了說明。根據該情節,應視為安某在獲知遺贈的情況后,即作出了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且安某的母親陳丙實際占有管理該房屋,故對上訴人主張安某未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進而對陳丁的房屋份額應適用法定繼承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解析】
本案核心問題在于實務中如何認定遺贈的接受與放棄。遺贈是指遺囑中指定的遺產承受人為法定繼承人范圍以外的人,且其只承受遺產權利而不承受遺產債務。在我國的遺贈制度中,關于遺贈的接受與放棄,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盡管繼承法明文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但如何作出意思表示、向誰作出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而本案就遺贈接受與否,涉及到以下三個問題
一、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的對象
繼承法明確規定,受遺贈人如接受遺贈,必須作出相應的意思表示。從立法原意出發,該等意思表示必須有相對方。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實務中向何人作出意思表示并不明確,成為了司法裁判面臨的難點。
從目前觀點看,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的相對方一般包括以下幾類: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等。通常,在大多數被繼承人的遺產并未設立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的情況下,法定繼承人被認為是接受遺贈意思表示的對象。問題在于,受遺贈人應向全體法定繼承人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還是僅向部分法定繼承人表意即可。實踐中有的法官認為,由于放棄遺囑繼承的表意對象為其他法定繼承人,故受遺贈人接受遺贈也可照此類比適用。此種觀點固然無可厚非,但是否要求全部法定繼承人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尚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就本案而言,受遺贈人安某為遺贈人陳丁的外孫,陳甲、陳乙、陳丙均為陳丁的法定繼承人。如意思表示的對象為全部法定繼承人,則安某必須向陳甲等三人均作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而陳甲、陳乙二人因與安某存在利益關系沖突,其二人不可能認可此類意思表示的發生,這亦在客觀上為安某課以較大的舉證負擔。事實上,一味要求受遺贈人向所有法定繼承人作出意思表示,實踐中并不可行,同時亦無必要。本案中,安某在知道遺贈事實時未滿18周歲,其法定代理人陳丙在獲知遺囑后,將遺囑情況亦跟李某說明。而李某陳述,其知道遺囑情況后,跟陳甲、陳乙作了說明。雖陳甲、陳乙對此不予認可,但李某及法定繼承人之一的陳丙都表示知悉接受遺贈的事實,故原則上,雖陳丙與安某有利害關系,但在有李某陳述予以佐證的情形下,不必要求全部法定繼承人都作為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對象。
二、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方式
認定是否構成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第二個重要問題在于該等意思表示應采取何種方式作出。一般來說,意思表示可以有明示和默示兩種。明示的意思表示方式包括受遺贈人以書面的要式行為或口頭的不要式行為,將其接受遺贈的意思表達于外、使人知悉;默示的意思表示一般表現為受遺贈人以事實行為來表達其接受遺贈,如占有或實際控制遺產等。
本案中,一方面法定繼承人之一的陳丙知悉該遺贈內容后以明示的方式,即通過李某經口頭方式就接受遺贈的意思向陳甲、陳乙進行過告知,此行為應視為安某本人明示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安某的法定代理人陳丙實際占有、管理涉訴房屋的事實行為,亦可以表明其以默示的方式對遺贈進行了接受。故基于上述考慮,并綜合全案情節,最終認定安某的行為構成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
三、如何認定是否接受遺贈
本案的核心、亦是最大的爭議問題,即如何認定遺贈的接受。對此繼承法僅有原則性規定,而缺乏具體可操作的規定。實務中,如何認定受遺贈人是否接受了遺贈并且作出相應的意思表示、以及如何作出該類意思表示,確實成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雙重難點。而本案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對解決此類實務問題的有益探索:即在認定受遺贈人是否接受遺贈時,原則上應采取較為寬松的標準和較為寬容的態度。一方面,這種選擇與實務中大多數法官的通行裁判思路不謀而合,有助于形成實務中統一的裁判思路;另一方面,在并無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限制性規定的情形下,法院不宜、亦不應該在認定遺贈的接受時,人為地設置障礙或提高標準,而更應尊重遺贈人在訂立遺囑時的真實意思。此外,從繼承法的立法原意來看,因受遺贈人的身份特點及受遺贈人無需負擔對應義務,遺贈需要區別于遺囑,作出明確接受的意思表示。從這個角度來說,受遺贈人只要有明確的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即可,無需為其舉證等被課以更多的負擔。因此本案在認定遺贈的接受上采取較為寬松的標準的做法,符合立法原意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